本篇文章4566字,读完约11分钟
李东军
民族和物种的变异
钱穆在“中西文化观”的基础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出了药方。以西方科学精神为医学指导,以儒家传统为医学,它仍然是一种中西药。
为此,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反对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他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旧书有所涉猎,大多数人对旧书不以为然,这足以证明新文化的弊端。尤其是崇洋媚外的风气,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疯狂和投机”。
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声称要与传统决裂,这要么是愚蠢的,要么是错误的,而且是适合子孙后代的。他想以牙还牙,高举传统,拉动传统文化的衰落,开创旧儒学的新局面。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梁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只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立场,这种暧昧的态度不仅缓和了儒家传统,而且表现出他自己的“困惑、疲劳和虚幻”,“不足以推翻陈独秀的思想,也不足以说服陈独秀的学派”。
你为什么这么说?再如梁的“不反对科学执政的西化”。如果你不敢“反对”,你只能被动地“弥补缺点”,而没有“积极有力的意义”,也没有“东西方文化之间不可能有庄严的区别”。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趋势反映了“救国救民”的变态心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治国理念都是以“救国保种”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新文化“总想改变物种”,认为“我们的物种”根本不可能存在于天地之间。因此,“转世的想法不是很吝啬,但它变成了深刻的痛苦和疾病的意义”,这是自我挫败的拯救国家。
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称为“失去了心的人”。所谓“赤子之心”就是爱国主义,因为“革除旧习”离不开“摧毁爱国主义”。只有摧毁爱国主义,才能“打倒孔家店”。显然,他把爱国主义与热爱国粹联系起来,认为国粹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一种崇高而不可动摇的文化象征。
在“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文化的精髓难以沉淀。为什么这个国家以此为生?在鸟巢下,这个国家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将国粹与国粹割裂开来,认为旧国粹不可移,新国家不可立,这与钱穆的爱国思想大相径庭。要救国,钱家首先要救国的国粹。只有国粹存在,国家才能存在;国粹消亡,国家也将消亡。

然而,所谓的“国家”是一种“国粹”,有一个空的时代,这与过去和现在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认为国家是历史进程中某个阶段和环节的存在。在政治演变中有必要改变它的形式。如果旧的国家制度束缚并危及全体人民的命运,它就断然否认其合理性,与之决裂,并在新的历史运动中作出新的制度安排。至于所有的旧文化遗产,不管过去多么神圣和美丽,只要它们阻碍了现在的生存,就应该从历史舞台上撤出来。

我们应该如何确认文化的价值?新文化的取向是,它不是在古物本身,也不是在欣赏古物的心态,而是有利于今天的人的生存,使他们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文化选择。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到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也受到中国社会内部专制压迫的威胁。因此,反帝反封建具有最高的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西方化与反帝、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局面。

然而,在钱穆看来,它是相反的,可能并不互补。爱国,应该热爱传统,这一点一目了然。他显然可以“反传统”,称自己为“爱国运动”,这是他无法理解或理解的。当然,与梁漱溟不同,他既关注传统又关注新文化运动。他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在两种情况下都有道理。他不会按照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去思考它。他的爱国主义根植于传统。正如他所说,它是“历史的延续”,是儒家传统的现代版;他沿着一个方向——儒家传统的方向思考,并发表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宣言。

历史的空虚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问题。
因为中国文化是在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他还强调,世界上没有民族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有一种精神贯穿了几千年。其他类型的文化通常随着国家的兴衰而兴衰,但会变化和消失。虽然有些文化曾经繁荣过,但它们就像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无法积累成一个深刻而巨大的文化实体。甚至西方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也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而衰落。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压迫和风化下,他们的光辉变成了一堆余烬。虽然它在现代被复兴了,但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了,远不如中国文化那样永无止境。

正是不断变化的历史促使西方人以哲学的眼光关注自己的文化,寻求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哲学模式,并赋予自己的文化一种不变的气质。另一方面,中国人不需要从超越历史的哲学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化,因为中国历史的永恒连续性已经使他们的文化显得根深蒂固,正如钱穆所指出的:中国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文化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中都有所体现,除了历史之外,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谈论文化。

钱穆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是基于他对中国永恒和持续的历史的信念。他坚信,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打破中国历史进程的永恒连续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态度是“快乐而知命”,这与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悲愤所表达的“同情他人”的危机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以西方历史的进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导致了先忧后恨的态度。他说:这种心理变化可以从陈独秀前后态度的变化中看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评价和各种不良后果。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历史中蔑视革命的任何人都是一切真正进步的敌人。在创新中,我们应该知道旧的,但我们不应该知道疾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刀医学?如果我们依靠空的抽象理想,努力工作并变得强大,寻求其实现,并摧毁裂缝,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结果将是毁灭而没有改善。新文化运动只是一种“新趋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不到建设性的作用。他没有对现代中国“挫折、屈辱、婴儿退休和没有进步”的历史视而不见。相反,他认为5000年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象征着中国生活的健康和繁荣,“过去的50年”是“生活过程中的症状之一”。“如果50年内没有疾病,就有必要把他的生命本身的原因埋葬5000年。”埋葬生命本身,只有自杀”。

显然,这次讨论是针对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在他看来,反传统只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自杀。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从进化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他们发现,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而现代中国社会各种疾病的成因,如只冻脚,都不是一天造成的。如果我们一味地赞美过去而不赞美现在,我们就不能根除中国社会的各种疾病,反而会使我们的国家身患绝症。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它并不是“举世无双,值得骄傲的”。虽然有汉唐盛世和世界四大发明,但也有民族的沉沦和萎靡。特别是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被征服的人和麻木不仁,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吃人”本性和中国人的奴隶本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是中国社会各种疾病的根源。

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并没有采取他自己所主张的“和”的态度,而是建立在一种对抗的立场上。因此,他无法理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国家和民族的难以忘怀的真诚,以及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脱胎换骨的选择。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
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不难发现,钱穆的长史观虽然表达了文化自信,却难以拯救世界,新文化的进化史观无疑更深刻,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钱穆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五千年的历史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任何保证。在长期消亡的古代文明中,哪个国家的文明史不到一千年?古埃及王国从兴起到衰落有将近4000年的可靠历史,但是它最终被波斯人摧毁了。面对自然选择的自然法则,古老的传统并不自然地享有生存权,它必须在残酷的竞争中检验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基于古代传统的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荣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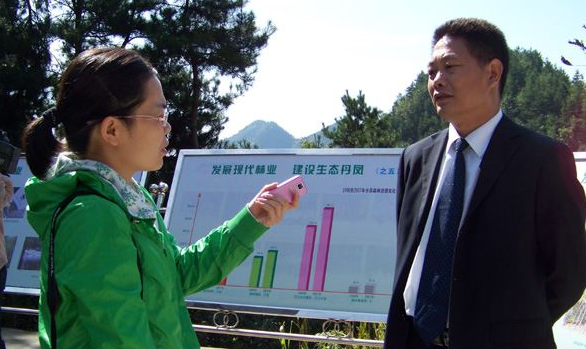
新文化的异化
钱穆继续考察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他认为:民国初年,政治道路坎坷,民族运动依然存在。由于当前的政治形势,“没有希望,却转向社会的普遍改善”,西方思想被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革新所引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有了发展的契机。
关于文学革命的意义,他说:从外部来看,文学革命的特点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但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文学观念的差异,说白了,这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争论。
因此,文学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道德革命,钱穆关于新观念、新道德的论述是这场文学革命的伟大成就。至于新文学本身,钱穆认为它还处于实验阶段,还没有成熟的形式。
在这方面,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理解,并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这三点。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旨在普遍提高社会道德思想”,“以西方科学和人民治理为标准”,“以实验态度为出发点”。这三点是有争议的,但总的来说,它们仍然是正确的方法。
但五四运动后,普通青年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越来越走向堕落和放纵的生活。就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它也从改善社会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转向了政治道路。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正确道路,偏离了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并使文化运动政治化,即被政治异化。
他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异化的影响:从激进的方面来看,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流,“近年来,共产主义青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使得“激进的青年以一定的速度参加了政治革命的实际活动,但马前卒过于激进”;从“隐退的婴儿”来看,许多新青年“逃进了文艺之路,却死于浪漫与颓废”,这使得“性刺激作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这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失势的落伍者”。

对于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疑古辨伪思潮,钱认为这只是清代儒学的考据学遗产,疑古的目的是“敬经敬圣”。如今,当人们怀疑古代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他们崇拜圣人和尊重经典的观点,而只讨论古代的历史。”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过去思考的深切感受”,相反,它动摇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之根,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国家5000年的历史,从而失去了走向未来的目标。因此,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已经完全进入了死胡同。

在钱穆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不仅没能引导新青年,而且在学术上也进入了一个狭窄而极端的角落。后来,“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形而上学之争”成了“特别为其余者”。他对当时新旧学校之间的辩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旧派“盲目守旧”,指责新派“心不在焉,以新为本”,认为胡适的“全盘西化”偏向科学,而梁启超、梁漱溟的本位文化偏向民族道德。

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他唯一信服的是戴的主义:戴所说的,是不是将来的针?
在他看来,戴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它既涵盖了两大派别,又具有革命生命力。他把这个“合理的主张”概括为两点:第一,恢复民族道德;其次,我们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科学。
这两点,也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计划,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是令人不快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科学精神和民族道德之间的差距,对不相容的一面视而不见。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民族道德自然是不合理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作为新的时代尺度,无情地批判传统,使传统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成为理性审判的被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极端”的“主义之争”。它是一个国家崛起时的生命力的体现。20世纪初,由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提倡,各种学说在中国盛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一种崭新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植入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结构和价值取向。

(作者接近“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
标题:同钱穆先生谈文化(二)
地址:http://www.pyldsnkxy.com/pyxw/8215.html

